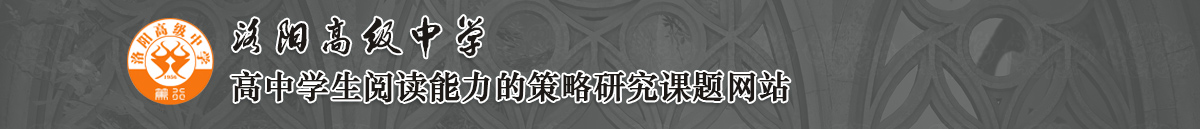时下的语文教学,人的教育被忽略了,语文成了工具,仅仅成为考试拿分的手段,成为学好其他学科的文字桥梁。于是,技能、技巧的训练在语文教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语文教育离“人”渐行渐远,越来越目中无“人”。
文言文教学是初中语文教学的重头戏,也是时下中考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一直工作在教学一线的语文教师,我耳闻目睹了诸多的古文教学课例,对此有“切肤之痛”。
在一次全市初中语文教师评优课大赛上,我的感受愈加深刻。为保证大赛的公平性,本次大赛选取了一篇教材之外的《项脊轩志》,由所有参赛教师同课异构。众所周知,《项脊轩志》是明代归有光的传世之作,文字浅近,情韵深远。但近十位教师执教的《项脊轩志》却令人瞠目:他们制作大量的课件,将这篇文章中出现的一词多义现象诸如“凡”“置”“瞻”等,古今异义词诸如“方丈”“往往”等,词类活用诸如“乳二世”中的“乳”、“雨泽下注”中的“下”、“垣墙周庭”中的“垣墙”等,还有其他涉及到的古汉语现象详细地提炼出来,并加以细致详实的解释;而后是请学生逐段把这篇课文译成白话文……整节课都是知识梳理和技能训练,文味全无,情味缺失。一节课就这样结束了,留给我的是太多的思考与反省:虽然基础知识训练得比较扎实了,但归有光寄寓在《项脊轩志》中的那份浓得化不开的亲情诉说呢?那份蕴含在字里行间的让人潸然泪下的因人生失意、家道中落而生发的孤寂与落寞呢?那份因看到庭中枇杷树而思念亡妻的物是人非的感伤呢?如此等等,在上述教学中学生均无缘体味。
无独有偶,后来笔者又听取了一位青年教师执教的诸葛亮的《出师表》,教学环节几乎和《项脊轩志》如出一辙,而对于诸葛孔明在《出师表》中表露出来的忠诚之心、鞠躬尽瘁之情,以及婉谏后主刘禅的政治智慧均无所提及。
有经验的教师都知道,在散文教学中,因为散文语言的纯美性、写作手法的灵活性、抒发情感的多元性等,散文教学无须刻意去寻找人文元素而人文自在。但时下的有些散文教学课已经远离了散文本身。
朱自清的《背影》是人教版语文教材八年级上册中的一篇教读课文,文质兼美,父子亲情感人肺腑,催人泪下。有位教师在执教该文时,首先引导学生初读课文、整理字词,接着由学生自主讨论理清《背影》的思路,最后要求学生:“如果你是中考命题人,就本文而言,你能命制出什么样的阅读题?”全班学生在一阵热烈的讨论之后,命制出近十道仿中考题模式的阅读题,老师在引导解题的同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一篇经典名篇,被理解得极其浅表,肢解得支离破碎,让我无言以对。那浓蕴文中的语言之美、情感之真、人性之善,在这节课上荡然无存!散文阅读练习化、试题化,“文”在哪里?“情”何以堪?
古文教学、现代散文教学如此,古典诗词教学、作文教学情况也不乐观。古典诗词教学基本是释义和强记,作文教学则侧重于文体或模式的训练,为迎合阅卷者的口味而强化作文套路训练。技能增强了,但不同的生命个体在文中的个性少了,棱角平了,思想俗了,情感淡了,代之的是教学流水线和标准模式。由此引发笔者思考:中学语文教学中的人文教育还剩下多少?中学语文教学到底怎么啦?
究其原因,一方面,许多学校在升学的压力下,过分地扬理抑文,不仅造成了学生知识结构上的某些欠缺,也直接影响了以形象思维、直觉思维为特征的文科思维能力的发展,淡化了学生对语文的兴趣。在此影响下,学生片面地认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学习上急功近利,过分重理轻文,兴趣单一。同时,广大的语文教师也在应试的大环境下,以“考纲”为教学依据,严格奉行“考什么,教什么”,教学内容教条化,方法单一化,并且推崇逻辑推理,强调技巧性,强化语文的工具性,直接影响了语文教学的文学意味和文化品位。另一方面,随着教育的专业化发展及人们求职生存的需要,人的教育被忽略,人力教育成为时尚,加上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在教育中的盛行,人们逐渐忘掉了教育的根本,忘掉了人的灵魂。
美国思想家、教育理论家赫钦斯指出:“教育的目的不在于制造基督教徒、民主党员、工人、农民、商人,而在于培养人类的智慧,发扬人性,完善人。教育应该促进人生价值的实现,即帮助每个人聪明地、愉快地、像样地活着。”目前,我们该怎样拯救日益缺失的人文教育呢?根本的做法,除了转变教师的偏激观念和学生的错误认识外,不妨在教法、学法上多动些脑筋。
首先,教学中不唯考试,应基于“语文”。语文教学重在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在支撑人生成长的知识结构里加重“文味”,教师在教学中应该摒弃为考试而教学的语文功利观,应尊重语文的自身规律。只有这样,我们在教学中才能心气平和地引导学生在抑扬顿挫的朗读中感受语文的音律之美,在对语言的品析鉴赏中品味中华语言的深邃丰厚,在对形象的把握中感受人性之善,在对故事的解读中领悟人情之真。如能这样基于教学,则事半功倍,基于教化,则人文斐然。
其次,学法上要引导学生学会知人论文。所谓“知人”,就是了解文章作者的生平经历、志向追求、家道渊源、磨难际遇等等。在日常教学中,很多教师会把这一环节等同于简单的文学常识介绍,其实不然——此环节的意图在于让学生清楚地了解到他将和一个什么样的人对话交流,直至走进作者的内心深处,甚至和作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忧其所忧,乐其所乐。这样,学生在学习其文时才会“胸有丘壑”,理解品味才会情有所依,不至于天马行空、“我心茫然”。学生只有融入作品,才能深切感受其中丰厚的人文元素,人文教育才不是一句空话。
笔者曾带着上次在初中语文评优课上的不甘,特地在初三年级执教了《项脊轩志》。预先布置学生大量地查阅搜集归有光的生平资料,课堂上大家共同交流,集体汇总,然后对归有光的生平形成几点认知:一、归有光生于儒生之家,虽衣食无忧,但命运凄苦:8岁丧母,18岁失去对他疼爱有加的祖母,28岁失去相亲相知的原配魏氏,46岁失去三个儿女,时年继室王氏过世。失亲之痛,几乎伴随归有光的一生,让他屡屡感受到生命的脆弱无常。二、一生经历8次科举不第,60岁才稍有收获,读书人内心的压抑不言而喻;三、大家庭的分崩离析,让他感受到了更多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带着这样的作者认知再来品读《项脊轩志》,学生们很快就感受到蕴含在字里行间的凄苦味。即便是从第一节优美的环节描写中,学生们通过一些字词的品析,也感受到作者这样的情味和心境。学生们普遍认为,该文开篇呈现的便是一种压抑:全段共180字,到处是带有不堪、被动、忍受等充满“负能量”的词语,如“旧”“仅”“老”“渗漉”“雨泽下注”“过午已昏”“不能得日”,即便是描写在轩中悠然惬意情景所用的也是“寂寂”“冥然”“斑驳”等词。可见“凄苦”已经深入归有光的骨髓,变成一种随处可见的无意识。
正是基于对归有光的深入了解,学生才对《项脊轩志》有了如此准确明了的品析,悲悯作者之苦,感怀文章之美。知人论文,不刻意强化人文,而人文自在终端,有了如此深入的体味,学生还会疏远语文吗?
再次,在教法上教师应不拘泥于成说,善于倾听另一种声音。善于倾听学生反成说的见解,也是对学生人文精神的一种润物无声的培养与鼓励。无需讳言,许多教师在语文教学中过分依赖甚至无条件地服从教学参考书上的说法,这其实也是导致学生在语文课堂上不愿说话,甚至最终对语文“敬而远之”的原因之一,因为学生很清楚,教参的存在也就基本否定了他们在课堂上的话语权。是啊,谁能保证在不看教参的前提下,能和教参上的说法一致甚至相同呢?与其做不到,不如保持沉默。殊不知,恰恰是由于这样一种刻板的教学方式,封闭了学生鲜活的心灵,扼杀了学生鲜明的个性。
雅斯贝尔斯说:真正的教育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马克思也指出:“人,双重地存在着,主观上作为他自身存在着,客观上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无机条件之中。”如果我们能充分关注教师与学生、读者与作者的心灵交流,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课堂上就会不断绽放因思想碰撞而产生的人文教育的火花。记得我在教授杨绛先生的《老王》一文时,启发学生品悟文本末段最后一句话:“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同时,我提示学生从人性的深处去思考(因为教参上是这么定位的)。学生们几经讨论,答案始终不能令我满意,因为和教参上的说法还有差距。最后一位同学怯怯地站起来说:“老师,我认为这句话无须涉及到什么‘人性的深处’,无论是杨绛先生还是老王,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都是普通人身上那种最本质、最质朴的善良,这种善良存在于未受世俗污染的每一个人的身上。”短暂的沉默之后,我率先为他鼓掌,我惊叹于这种拨冗就简、变深为浅的见解,我折服于这种不同于教参的“另一种声音”。其实,只要我们关注心灵,尊重个性,这样的“另一种声音”就会不断出现,这难道不是实现人文教育的另一种途径吗?
总之,只要初中语文真正走上一条尊重语文本身规律,关注人的心灵、尊重人的个性的教学之路,以文化本位取代技能本位,以价值理性来升华工具理性,那么逐渐缺失的人文教育一定会回归初中语文教学课堂。
(作者单位:江苏省徐州高级中学)
(原载于2014年10月《初中生世界》教学研究版)